|
永远的怀念孙晓芬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。时间越久远,对他的思念和记忆越深刻!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,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来得格外晚,已是三月中旬仍春寒料峭、寒气逼人。当我匆匆赶到医院,病床上的父亲昏睡不醒,呼吸急促,打着点滴、吸着氧。我摸摸他早已谢顶的上额,烫手。守护在旁的姐姐告诉我:父亲高热不退,时而昏睡,时而清醒,但昏睡多于清醒。一种不祥的征兆笼罩着他。看着被疾病折磨得形销骨立,蜷缩在病床上的父亲,两只深陷的眼睛泛不出一点光亮,毫无反应地看着我。我感觉胸前一阵阵疼痛,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他再也不是曾经驰骋疆场的热血斗士,激情满满。再也不会像永动机一样勇往直前,不知疲倦地运转。 父亲和所有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兵一样,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洗礼,身上留着战争的痕迹。他左小腿外侧有一伤疤,那是弹片嵌进皮肉留下的。左颌下和右面颊各有一疤痕,当咀嚼吞咽时显现出一分硬币大的凹陷。记得小学五年级暑假,一次在饭桌上姐姐无意间看到他面颊的凹痕便好奇地问他,他随口答道:“枪伤”。我们听了一下子好奇心泛起,怎么回事?父亲告诉我们:“当时他所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先遣支队,向驻扎在莱芜的日军发起突袭,枪声响起,他和战友率先冲进敌营,一场激战消灭了数百伪军,看到堆成小山的战利品喜出望外,这时感觉到下巴颌儿热呼呼的,用手一摸粘粘的,血浸透了他的上衣,挂彩了!子弹是从左面颊射进,右下颌穿出的颌面贯通伤”。我们惊叫:“好险,好险!再高一点就没命了……”话音未落,父亲开怀笑道:“死了也值呀,直捣鬼子老巢,是抗日战士最高的荣耀和追求”!接着又指着自己的面颊诙谐地说:“如果子弹再高那么点,兴许还会有对酒窝哩”。云淡风轻的语气中透着些许惋惜之情,这更令我们目瞪口呆,这玩笑开得太大了,简直就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一番生死笑谈。 那是第一次听他讲自己的故事,带给我的是一种心灵的震撼。平时读到、看到的战争故事和电影大片,许多也很惊心动魄,但都不如亲身经历过的人讲述来得真实和具有冲击力,更何况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。之前,我从不关注,也未曾听他讲过自己的故事,无从知晓他的战争经历和过往。但我知道他珍藏着两个心爱的“老伙计”,一支勃朗宁手枪。勃朗宁手枪就放在他枕头下,每晚陪伴他入睡。后来他按规定把手枪上交组织。我猜想他上交时,心里不知有多么不忍,多么不舍!那是他在战场上与鬼子生死博斗用生命换来的。那把日本军刀曾挂在他的床头,刀身足有两尺长,刀尖微微上翘,闪着逼人的蓝光,锋刃上约三公分锯齿状残缺,是战场上短兵相接、你死我活残酷搏杀的见证。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刀擦得铮亮,像勇士般高高举起,潇洒地左挥右砍,威武而霸气。每当这时,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骄傲,对他由衷地敬佩和崇拜。 一天一夜过去了,父亲从昏睡中醒来,衰弱疲惫的他体温降了下来,感觉饿了,我们赶紧煮了面疙瘩汤,他喝完躺下休息了会儿,看起来精神好多了,自言自语道:“我是要去见马克思了……”我们面面相觑,不知如何回答。他接着说:“那么多战友都走了,有的连尸骨都没找到。几十年过去了,好多老领导老战友也离开了,该去找他们啰”。这让我想起似曾相似的一幕:之前他患胃癌作胃大部切除术,当术后醒来见我们焦急的围在身边,便打起精神道:我命真硬呀,这辈子闯过了一道道鬼门关,睁开眼还活着,这便宜占的够大呀!一句话就让我们揪紧的心松了绑。最懂他的莫过于几十年的战友和老伴一我们的母亲,她曾对我们讲述:“那年头三天两头打仗、常有战友牺牲,我们随时做好死的准备。死亡见太多了,心也麻木了,也不会哭了。如今老了老了,爱回忆过去的事情,爱动感情了。每走一个(战友)就动一次情,尤其是1号首长(张国华)病逝,你爸哭得那个悲痛欲绝”!那时听了母亲的话,我还不明白:难道比亲娘老子还要亲?现在我懂了: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结下的战友深情,是经过枪与炮的洗礼,是在刀光剑影中淬过火的,是鲜血凝成的过命之交。这种感情与我们和平年代的战友情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!看着面前被疾病困扰,历经残酷战争考验,新中国刚成立又转战西藏高原,在高寒缺氧恶劣条件下长期驻守雪域边防,文革中遭受身心摧残和磨难的老父亲,我的心好痛!好痛!他对生命的认知是那么透澈,面对死亡才会如此豁达坦然。 那一天,他断断续续讲述了我们从未听过的往事: 他15岁那年(1937年12月)鬼子占领济南,1938年1月相继占领泰安、济宁、青岛……对他的家乡烧杀掳掠,国破家亡。1938年2月他和村里的热血青年参加了抗日组织“罡风道”,打击日寇、保卫家园。他们夺武器、炸桥梁、抢粮食、捅炮楼,抓汉奸。配合八路军对日冦进行反扫荡。1938年6月被八路军山东纵队收编,从“罡风道”抗日自卫团员成为八路军战士。他们行军打仗、风餐露宿。 一次,部队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小村庄,那些日子常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驻地转悠。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,部队接到命令连夜转移。当天色渐明,才发现队伍后面跟着那丫头,无论怎么劝说让她回去,她坚决不肯。就这样跟着部队走上了革命道路,成了一名抗日女战士,再后来她就成了我们的妈妈。 父亲孙治平(左)和母亲任传珍(右),摄于孟良崮战役后 后来部队整编归属二野刘邓大军,参加了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,历经艰难险阻浴血奋战,终于打败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整编74军。紧接着1948年底,又接上级指令秘密夜行,直扑枣庄临城配合中原野战军、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部队艰苦作战,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。随后挥师向南,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。 1949年姐姐出生在河南偃师,跟着父母在马背上随部队渡江南下,向四川挺进。1952年我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庄园。刚满40天就送到18军安仁保育院,由奶妈喂养。3岁多母亲去保育院看我,我叫她阿姨,这让母亲难过了很久。父亲说他送我回保育院,一路上我抱着他亲了又亲,不停的叫着我的好爸爸,好爸爸。当分别来临时,我死死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,最后被老师强行抱走,当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叫声,想想又是几年不能相见,他心里很难过。这时我才发现父亲也有儿女情长的另一面。他不无感慨地说:“部队驻守西藏,只能把你们姐妹俩留在后方保育院,从小过军事化管理的生活,在部队的关怀下长大,你们就是军队的女儿呀! 那天父亲和我们说了许多父女间的心里话,我真希望时间可以凝滞,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,没有疾病也没有痛苦,没有生也没有死,就这么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倾听着、依偎着。何曾想,那是他生命极限挑战的回光返照,是我们父女间离别前的最后时光,它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回忆。 傍晚时分,他的病情急转直下,医院下了病危通知。当又一个清晨来临时,他人生最后一个工作岗位的老战友钱春华伯伯、乔学亭叔叔、白健叔叔、王心前叔叔、杨德福叔叔等来到病床前,神情凝重地看着他,与他作最后的诀别。杨德福叔叔俯身在他耳边说:老首长,我们看你来了。他微微睁开双眼,迟钝无神地看着前方,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。姐姐贴近他耳边大声呼唤他:爸爸,爸爸,我们和妈妈都在你身边,叔叔伯伯们都来看你了。他缓缓地抬起头,目光恍惚而涣散。他不再认识我们和他的战友,他进入了谵妄状态。他的手无意识的在被单上摩挲着,像是在找什么东西,当他的手触摸到我的手指,颤巍巍地抓起就往嘴里塞,并不停的吮吸,从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:“这烟味淡咯……劲儿不大,不呛口哦……”我把手指抽出来,他又在被单上继续摸索着,当触碰到血压计,他摸了又摸,拿不起来、却又不舍放下,嘴里喃喃低语:“枪…枪…老伙计呀…”说看用食指做了个抠扳机的动作,“嗯哼…又撂倒一个……干得漂亮!”他呼吸急促,大口喘息了好一会儿,突然又伸出手在半空中划拉着,“来,喝酒……庆祝胜利.…,酒好哦……大肥肉呀……真香哦……”喘息片刻后,他吃力地抬起低垂的头,用手指着天花板,微弱而急促的说:“飞机、飞机,是……XX飞机,快……”他使劲用双手撑着床,挣扎着想坐起来,可羸弱的身躯不再受精神支撑,重重地瘫倒在了床上。我悲痛至极、泪眼模糊地目睹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我知道,弥留之际的他回到了热血澎湃的青年时代,徜徉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。这烟、这枪、这庆祝胜利的酒和肉…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,与他的理想信念一起早已溶化在灵魂深处,至死不渝。 我们一遍遍呼唤着他,真希望他能醒过来,面对死亡再作一次幽默谈笑。父亲走了,走得平静而安详,他回到深爱着他的亲人身边,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,回到曾与他并肩作战已在天国的战友中…… 后记 父亲去世后,从成都军区治丧委员会的悼词和“战旗报”刊登的讣告中大致了解到他的简历,见附录一。 2021年底,父亲同乡老战友郑志士伯伯(原武汉军区参谋长)之子郑金陵联系到我们,把“八路军山东纵队前辈资料”中有关父亲的资料转发给我们,让我们对他的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,在此特别感谢郑金陵,并将父亲简介摘录如下,见附录二。 附录(一) 附录(二) 作者简介: 孙晓芬:1969年3月入伍,总后渝办三二四医院卫生兵。1971年~1974年就读于第七军医大学医疗系。服役于成都军区后勤部军事医学研究所(现: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),历任:研究实习员,助理研究员,副研究员,副主任医师,己退休。 聚聚玩官网 http://www.youzhuan3.com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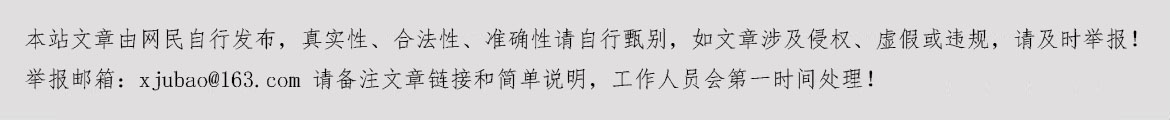
|